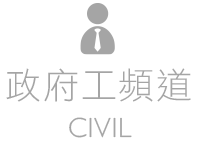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些問題看似面試時常問的「你的缺點是什麼」,而「我工作時太拚命」之類的回答,則幾乎沒透露出什麼,所以這類問答幾乎已經變成一種「如何輕描淡寫」的遊戲,因為太怪異或瘋狂的回答都可能害自己無法過關。文:妮洛芙・莫晨特(Nilofer Merchant)
缺乏信任,無法擴展
地獄是萬物毫不相干的地方。——但丁
TED夥伴:歸屬有其代價
儘管湯姆・瑞利(Tom Rielly)百般不願意,他還是開除了黃頤銘(Eddie Huang)。
黃頤銘違反「TED夥伴」(Ted Fellows)計畫的規定,在為期七天的TED研討會第四天溜出去。湯姆收到其他十九位TED夥伴的電子郵件和簡訊,通知他黃頤銘缺席了。參與該計畫的要求不多,其中一項協議是參與者必須在那裡待上整整一週,不得中途離開。
湯姆終於打電話找到黃頤銘時,問道:「怎麼了?」那時黃頤銘正開車前往洛杉磯參加一場公關活動。黃頤銘在Instagram上記錄自己的動態,湯姆想知道他為什麼會在過去二十八小時內擅自脫隊去看湖人隊比賽,又和朋友共進晚餐。雖然湯姆勸黃頤銘趕快歸隊,黃頤銘說他還有幾件事情要做。湯姆覺得黃頤銘根本是得寸進尺,所以在電話上把他開除了。
黃頤銘隨後利用他上廣播受訪的機會,談到那次參加TED的經歷,也談到知名的TED研討會背後有何寓意。
「那跟邪教沒什麼兩樣。」黃頤銘說:「我去那裡整整一週,只能聽別人告訴我該做什麼、該去哪裡,實在太可怕了……他們每天安排十三小時他媽的活動。」黃頤銘是餐廳老闆,也是回憶錄《菜鳥新移民》(Fresh Off the Boat)的作者,他雖然自願加入TED那個團體,但顯然跟他們不對盤,現在他說那個團體是「山達基夏令營」(編按:山達基是創立於美國的一套信仰與修行體系及宗教,因其作為而飽受爭議)。
我們都曾經參與過可以隨心所欲加入及退出的團體。成員看待那種團隊的方式,就像我們處理健身房的會員資格一樣:那種團隊隨時都在,方便我們隨時加入或退出。成員有所「歸屬」,但那完全是他們自己的關係。幸運的話,我們也會參與到休戚與共的團體。當我們離團時,團員會想念我們,我們和其他團員有共同的夢想,也會關心及祝福其他團員的成就。這種互動的團體不會自動發生,需要做某種投資:投資我們自己。
湯姆開除黃頤銘後,是否感到後悔?那件事發生在二○一三年,距今已過了好幾年。湯姆歎了口氣,看向別處,沉思了一會兒才回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想最近的新聞:黃頤銘的著作改編成電視劇,但最近黃頤銘也跟那群人公開鬧翻了。《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報導稱讚那部電視劇:〈黃頤銘,向世界造反〉。但湯姆回答我的問題時,並未提到那件事,他說:「那個決定是對的,因為黃頤銘不願合作。」但是他又補充:「如果一切能重來的話,我的反應或許不會那麼情緒化。」
TED夥伴計畫的種子是在二○○七年播下的,當時TED邀請一百位年輕的創新者出席TEDAfrica大會,其中一位與會者是十九歲的威廉・坎寬巴(William Kamkwamba),後來他改變了湯姆的人生。威廉十四歲時,利用垃圾場撿來的廢物自學打造成風車,原型是根據他從圖書館借來的書上大略的平面圖。當時他無法就學,因為他的國家馬拉威正經歷饑荒,他的家庭務農,沒有足夠的收入讓他上學。威廉的故事深深打動了湯姆和TED的所有觀眾,所以湯姆和其他的研討會籌劃者開始思考,如何讓像威廉那樣的人——創造驚人成就的新鮮人物——成為TED固定的一部分。
TED是technology、entertainment和design(科技、娛樂與設計)的縮寫,後來發展成涵蓋任何「值得傳播的想法」。
二○一五年,TED慶祝成立三十週年,但牛津大學畢業的媒體大亨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於二○○二年收購TED時,TED只是一個為精英族群開辦的研討會,只有數百位美國富豪有資格參與那個論壇。克里斯想保留原來的優點,同時為那場聚會浥注新的活力和觀點。他藉由贊助TEDAfrica、TEDIndia等單次活動以及如今每年舉辦的TEDGlobal來增添全球視角。他也授權大家在網路上把TED演講免費分享給任何人,那成了大幅擴大TED影響力的轉捩點。克里斯和他的團隊也發起了TEDx架構,允許任何人獨立籌劃在地的研討會,以便與當地的社群分享有價值的想法。在本書撰寫之際,這類活動已舉辦了上萬場。
受到TEDAfrica演講的啟發,湯姆說服了克里斯認可建立全方位的夥伴計畫很重要。湯姆身為TED的總監,一直以來負責審核每位TED與會者的申請書,所以他能適切地判斷TED需要什麼。他創立PlanetOut——曾是LGBT社群最大的線上資源——並擔任董事長時,就已打響社群達人的名號。湯姆以前難以對父母出櫃,所以他總是設法營造友善的空間,讓人感受到被接納。
曾在Google及推特擔任主管的凱倫・維克(Karen Wickre)認識湯姆數十年了,她認為湯姆的獨一無二是「來自於超容量的頭腦和心胸,它們包納了他對世界及每位他所遇到的對象所產生的強烈好奇心。幾乎每個人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就把他當成朋友。但湯姆還有一個天賦,他知道如何營造出環境,讓大家一起合作的成果更勝於各自單打獨鬥。」
湯姆已經準備好、也願意把「TED夥伴」這個願景轉變成現實。但後來那個計畫的演變及開花結果的過程,套用之前安德烈的說法,是逐步展開的。
維繫我們的連結
如果把理念轉變成現實的人不知道該如何塑造共識,任何理念都沒有機會成功。因此,「我們的力量」不是指任何群體的絕對人數,而是指成員之間的連結,例如好奇心、弱點、處理衝突的能力。想要實現某個理念,每個參與者都需要知道如何維持一定的好奇心,從而發現該解決的問題。他們在探究有哪些選擇時,需要傾聽彼此;也要適度地示弱,接納彼此的協助。此外,面對棘手的決定時,他們需要共同爭辯一番。如此一來,到最後他們便能在採取行動時相互依靠。
少了那些連結,每個人等於是單打獨鬥,跟那些能協助他們變得更好、做得更好、獲得更大成就的人毫無聯繫。
所以,如何建構那些連結呢?
為什麼是我?
「哦,天啊,我是怎麼進這個房間的?」住在紐約的伊朗裔搞笑演員及電影《穆斯林來了》(The Muslims Are Coming!)的導演奈金・法薩德(Negin Farsad)還記得自己被招募加入二○一三年TED夥伴計畫時的感受。她對那次經歷的描述,跟其他的TED夥伴很像:「我們每個人都想知道我們在那裡做什麼,也不知道我們是怎麼被徵召的。其實九九%的TED夥伴根本沒有財力參與TED,光是一張門票就要至少七千五百美元。我們在一些相對狹隘的領域裡確實有兩把刷子,但是如果沒有夥伴計畫,我們沒什麼資歷或財力擠進那個殿堂。」另一位TED夥伴是網絡科學家艾瑞克・柏若(Eric Berlow),他附和奈金的感受,因為他也覺得「為什麼有人會把我考慮進去。」
為了招募這些人,湯姆和同仁是從各個學門尋找多元人才,接著再以類似下面的問題將他們分類:「你不想讓別人知道你的哪些資訊?你討厭自己的什麼?你最不擅長什麼?」
這些問題看似面試時常問的「你的缺點是什麼」,而「我工作時太拚命」之類的回答,則幾乎沒透露出什麼,所以這類問答幾乎已經變成一種「如何輕描淡寫」的遊戲,因為太怪異或瘋狂的回答都可能害自己無法過關。
但是,湯姆之所以這樣問,不是為了知道「你有多會輕描淡寫,而是想知道你多會展露自己,我會注意聽很多東西,」他如此解釋,「包括你有多少自知之明,多謙遜,願意展現出多少脆弱與真實。」因為他主張:「如果你的回應像公司面試那樣虛假,你可能不是很開放,但TED夥伴需要開放。」
湯姆認為「開放」是滲透到這個不斷變遷的世界。
人才招募者大多想知道你是否做足了功課,並且花了上萬個小時準備好來投入預先確定的工作。湯姆確實想知道你對某個領域是否熱切投入,以及你在那個領域的表現是否優異,但他顯然更關注聰明才智以外的事。聰明才智只是衡量你知道的夠多,但「開放」是想向他人學習的求知慾。「因為不管你個人多優秀,當你不願開放接納他人時,就無法再進步了。」湯姆解釋:「開放自我的唯一方式,是充分接納自己……最極端、最古怪的自己。」
相關書摘 ▶《從1到1+》:網路請願書讓網友的鍵盤支持,就是在發揮議題影響力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從1到1+:每個人都能成為影響者,驅動社群力,召喚盟友一起改變世界!》,馬可孛羅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妮洛芙・莫晨特(Nilofer Merchant)
譯者:洪慧芳
有一種影響力,是你察覺自己夠特別!
★★全球頂尖意見領袖 妮洛芙・莫晨特暢銷力作★★
你是否曾提出點子,卻被視為「怪咖」並邊緣化?
或受「冒牌者症候群」所苦,連表達都不敢只因為覺得自己沒有「權力」?
美國知名思客告訴你,地球上七十五億人,人人皆有價值可以貢獻。
這是一場創新的風暴,而且就從你開始!
- 「黑名單」計畫的啟動,讓體制外的編劇也有出頭天,拍出了《貧民百萬富翁》、《王者之聲》、《鴻孕當頭》和《逐夢大道》等好萊塢賣座電影。
- 從#changetheratio到TheLi.st,科技職場女性有了凝聚多元背景及技能、支持「她們」的跨領域網絡。
- 美國非營利組織100Kin10在歐巴馬提出的願景號召下,以極少的人力排除萬難,即將在短時間內培訓出十萬名數理科教師。
這些故事的共同點,都是從「個人」開始,提出創新的點子,從而引發了一場改變的風暴。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Source